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帐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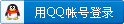
x
对语言的重视 ——读廖小权之《刺绣人生》 文/月照流水 没有语言,就没有文学。或者说,没有好的语言,就没有好的文学。 文学理论把语言界定为是文学的第一要素。(其实,作家的风格,作品的民族、地域性,也都是通过语言的载体表现出来的。) 文学写作的情感特征,要求将情感有形化和特征化。也就是,将审美的注意力放在生活原形的细节上,将构思时的想像、思维放在细节的提炼和表达上。(其实,就是让细节变为情感表达的意象符号。) 《刺绣人生》突出地表现了对语言表达的重视。比如:村庄长出了城市;奶奶身边闪出了儿时的院坝;到奶奶的刺绣中去找奶奶吧等等。 小说是说事的艺术,也可以借助于事,表现情感意蕴。这虽然不是主流,甚至混淆了散文与小说的界限。但从创新开拓的层面上,该作还是带来了闪小说创作的审美新鲜。
我们当然可以执著于小说的事,是否合乎逻辑,是否百转千回、可以拍大腿的出人意料、惊奇险怪等等,但都不应与“审美是文学的根本属性”相抵触。新闻差不多既是实有也是真实的,但新闻从来不是文学。 读了《刺绣人生》想到不久前程会长分享的两个创作基地的实况,基本都表达了以创新与开拓的精神来繁荣共推闪小说之发展的宗旨。随抹观感,以供交流、讨论。 附文: 刺绣人生
文/廖小权
院坝边苕花开了,奶奶脸上也笑开了花。她把绣花架子搬到苕花旁,看着花儿飞针走线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就可以爬到奶奶脚边,轻轻抚摸她那双怪怪的小尖脚,奶奶一点儿都觉察不到。
后来,村庄长出了城市,苕花被挤到花盆里。每次回家,我总看见奶奶注视着花盆,停下针,摇头叹气。
我出国离家时,苕花开了,奶奶一边看花,一边走针,脸上又开出一朵微笑。我停下脚步,静静地看她,蓦然,奶奶身边闪出了儿时的院坝。
等我归来,奶奶的苕花绣好了,在架子上随风轻颤,奶奶却不见了。我急得满大街寻找,一边跑,一边喊。
我喊了三天三夜,奶奶没有答应。我只好回到家里,收好奶奶的刺绣。睡在床上,我记起很久前奶奶说过,妞儿,有一天奶奶不在了,你就到奶奶的刺绣中去找奶奶吧。
我一骨碌爬起来,展开奶奶的刺绣。没开灯,室内突然亮起来。奶奶绣的苕花一瓣瓣展开,画面越来越大,苕花蕊中伸出一条熟悉的石板路,我沿着路跑去。一座熟悉的石木房子,院坝边苕花正艳,奶奶坐在刺绣架前,微笑飞针。
我悄悄爬到奶奶的小脚边,轻轻摸去。奶奶突然又不见了,她可是我唯一的依靠呀,我急得哭起来。
房子变成了土墙草房子,奶奶在烧饭,我冲进灶屋,趴到奶奶的身上。
奶奶又溜走了,我抱着的只是奶奶的相框。
|  |闪小说作家论坛|手机版|触屏版|小黑屋|闪小说阅读网
( 闽ICP备2025097108号-2 )
|闪小说作家论坛|手机版|触屏版|小黑屋|闪小说阅读网
( 闽ICP备2025097108号-2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