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帖最后由 小草青青 于 2015-12-27 19:08 编辑
(1)冬至
文/阿雨
看着妻子痛苦的样子,男人的心就像这雪夜吞噬了屋子,没有光亮。
还是女儿出生后,妻子就患上了风湿病,现在病攻心脏,右手变形,手指不能弯曲,脚不听使唤。
前天,女儿出嫁,妻子支撑起麻杆似的身子,高兴得两天没合眼。送女儿回来,又倒下了。
女儿出嫁,没陪送东西。男人是铁路集体工,夏季出去修铁路挣得少,冬天放假没有工资。妻子把家里仅有的三万元钱给了孩子。
男人问,明天孩子三天回门,上饭店吧?
妻子说,钱给孩子了,这回咱家可没钱了。
男人说,没就没吧,不能亏待孩子,你看病再想办法。
妻子说,这么多年都没看好,不看了。
借着门缝照进的一线灯光,男人望着床上妻子,心又是微微一动。可能是分床太久了,他总是偷偷幻想别的女人,可他有色心没色胆,他曾对妻子有过隐隐的恨。
妻子半天不说话了,静静地躺着,长有雀斑的脸格外苍白。男人离开沙发,轻轻地,一步一步向床,颤抖着向妻子伸出右手。
妈呀!妻子不知哪来的力气,猛地坐起,闪着惊恐的目光。男人吓怔住了。
妻子捂着胸,平静地问,你要捂死我?
男人搂住妻子,脸贴着脸的说,我想试试你鼻息。前天女儿走,哭着让我看着你,你有个三长两短,让我第一时间告诉她。
妻子哭了,孩子很幸福,我不惦记。我还有两万块钱,是我看病给你剩下的过河钱,我死了,你要找,就找一个吧。
男人哭了,别胡说了。
妻子说,明天是冬至,孩子回来,咱们吃饺子吧。
男人嗯了一声,看了看屋子,明天张罗卖房子,接着给妻子看病。(2)冬至
文/九泷十八滩
“田水同志,你与许行交往深吧?”专案组长林锋作风霹雳谈话单刀直入。
“没什么私交,许行做市长时,我任副市长,都是公事公办。”田水话语轻松,一副弥勒佛的表情。
退休两年,田水正为自己颐养天年不必身履险地而欣慰。
天有不测之风云,许市长因贪污受贿被双规。
这天,田水被通知到麒麟山5号楼喝茶谈话。
“没什么私交?,就是有一些私交嘛!”林锋抓住话柄不依不饶。
“工作中小吃小喝会有,人嘛不能说一尘不染,但我保证在职时两袖清风。”
“你是主管市里的地铁建设工程的……”林锋话说了一半,两眼紧盯田水。
“哈哈哈,林组长问得好,这项惠民工程,公开透明上级表彰,早有结论有案可稽,有账可查,恐怕不用这里再问!”田水说完,喝了口茶。
“你慢慢想想,设计过程中,许行有没有什么特别指示。”林锋边说边给田水斟茶。
“都是专家的设计方案,路线有些改动也属正常。林组长,党纪国法像一根鞭子,鞭子下牛都会前行,人更要有所畏惧呀。”
“当然。你先回去想想,想到什么随时可以来举报。”
回到家里,田水寝食难安:地铁改了线路!许市长交待他,线路要多惠民。线路多拐了一个大弯,几个地铁出入口的在建地盘迅速升值,地产商送了200万元给他,当然许市长……人啊,贪字得过贫!
冬至那天,田水坠楼身亡。
家人说:田水退休后,一直有病,长期失眠,患了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。
(3)冬至
文/孙子故里
他是天文学家,说起天体运行头头是道,夫妻生活却寡淡乏味,更不懂得浪漫情调。她身在官场,耐不得寂寞,只好逐波趋浪地下情。不料,一个不懂浪漫的人居然也知道捉奸,没办法,她只得痛下杀手,用氰化钾将他送往西天。
没有想到的是,他一命呜呼,居然阴魂不散,要找她算账。认输不是她的风格,她决心与他缠斗到底。
她巨资求得高人指点,和变鬼的丈夫缠斗了七天六夜。这段日子,她在家中摆坛设符,弊住窗户,死鬼始终没能进得了家门。
只要熬过这最后一夜,她也就可以彻底摆脱这个死鬼了。
最后的一夜虽然漫长,但太阳终归是要出来的,只要熬到卯时三刻,死鬼就不得不去他该去的地方,她期盼已久的新生活也就开始了。
房外,死鬼在哀嚎,时断时续,她的身体随着哀嚎抖颤,她两眼盯着时钟,恨不得卯时三刻马上到来,恨不得太阳马上升起。
卯时三刻越来越近,她的嘴里不停地倒计时:“还有五分,还有三分……还有,快!快!还有五秒,四秒,三秒……卯时三刻!卯时三刻到了!卯时三刻终于到来了,姑奶奶我终于熬到胜利的时刻了!”
她激动万分,连蹦带跳,高声呐喊:“死鬼,去死吧,姑奶奶我胜利了!”
她欢呼着,一路奔向紧闭了七天七夜的窗户。
窗户拉开,她惊诧不已,窗外居然没有光明,还是一片漆黑。
这时,一双冰凉的大手卡住她脖子:“亲爱的,夜晚还没有结束呢,告诉你,今天冬至,昼最短,夜最长,太阳升起在辰时!” (4)冬至
文/王福日
冬至。
大清早下了一场雪,天依旧阴沉地像围上了一层幔布。我和小外甥宝儿裹着棉被,躺在火炕上享受着灶膛的余温。
激烈的狗叫让我们坐起身,看到一个男人站在栅栏外探头探脑。
我披上棉袄走了出去。
“宝儿是在这吗?”看得出他衣装考究文质彬彬。
“你是……”我确定没有见过这人。
“我是他爸爸。”男人说。
……
长久的沉默,直到父亲趿拉着一双棉拖鞋走过来。
“宝儿的爸爸。”我说。
父亲浑浊的眼睛立即变得我从未见过的凌厉,“滚!”他说。
“我想见见宝儿。”男人说。
“滚!”父亲甚至不愿多说一个字。
“求求你了,我现在就只有这一个儿子了!”男人哀求。
天上又开始飘雪,落在男人的脸上,化开,也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雪水。
“你还是走吧!”父亲叹气,但语气仍是十分坚定。
男人背着漫天飞雪蹒跚离去。
姐姐十年前去城里打工,第二年就回了家,人逐渐消瘦,肚子却大了起来。她说孩子是工厂老板的,他有家室,知道姐姐怀孕,他让姐姐把孩子打掉,姐姐也是个执拗的人,不声不响离开,他们就断了。父亲说姐姐伤风败俗,姐姐气上加气,在生下宝儿的第二年就病逝了。
一场急雪下完,我们依旧立在雪里,头上雪白,也没想到去擦。
宝儿见我们良久不回,找了出来,“那个人是谁啊?”
“是你爸爸。”我说。
“哦。”宝儿从地上掬起一个雪团,向男人离去的方向掷过去。
“我们回家吧!”宝儿扬起笑脸,执拗地像他妈妈一样。 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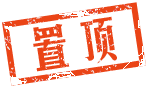
 |闪小说作家论坛|手机版|触屏版|小黑屋|闪小说阅读网
( 闽ICP备2025097108号-2 )
|闪小说作家论坛|手机版|触屏版|小黑屋|闪小说阅读网
( 闽ICP备2025097108号-2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