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帐号?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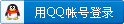
x
本帖最后由 飘尘 于 2019-9-28 22:29 编辑
故乡的灯
文/唐光源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最难忘的是母亲的菜油灯。菜油灯是土陶做的,大约一尺高,上端如碟子,里面加入菜油,再放进灯草。晚上,母亲陪我在灯下做作业。菜油灯的灯光不够亮,母亲便在灯盏里多加一根灯草。母亲在一旁给我缝补衣服。等我做完作业睡觉时,母亲便把油灯里的灯草减少一根,为的是省油省钱。菜油灯光,把灯下慈母的形象,深深地留在了我心中。
那时,边城没有电灯,多数边城人家点的是菜油灯,少数家境好的,点煤油灯,罩着高高的玻璃罩,比菜油灯亮许多。边城的夜市,有卖烤苞谷粑,耢醪糟蛋,豆腐脑等小吃。在卖家门口街沿上,支着锅灶,摊子上照着菜油灯。为了遮风,灯用红纸罩罩着。灯罩透出的红光,把边城的夜照得暖暖的。那些小吃的香气,飘着浓浓的乡情。
还有一种桔子灯,是边城娃娃们喜欢玩的。它是把大红桔子掏空了心,然后放入一小段蜡烛,用小木棍穿线提着。于是,满街的红桔灯,飞来飞去,还有娃娃们的嘻笑声。
每逢中秋节和元宵节,边城便要点字灯。在横跨街道的楼台上,用菜油灯摆成吉祥的字句,祝福边城和边城百姓。字灯与街沿的红灯笼,和谐辉映。
还有一种灯,是边城更夫提的马灯。边城人叫更夫为打更匠。我看见的打更匠是一个瘦高个中年男人,身穿着洗退了色的蓝布长衫,背有点驼。他应该有大名的,但大家只叫他打更匠。那时,边城人家有时钟的不多,白天看太阳,晚上听打更,安排作息。 更夫在晚上大约九点钟左右开始打二更。这时,母亲便催我上床睡觉。为什么不打一更,我不知道。五更也是不能打的,五更大约是下半夜五点钟左右,那时如果打更会招鬼进城的。是不是这样,无从考证。 更夫一手提着马灯和一面铜锣,走一阵,敲两下锣,喊着小心火烛,谨防贼盗。马灯灯光在街道上晃动,铜锣声在夜空中扩散,显得阴森可怕。有时,更夫把铜锣敲得很响,敲得不停,一路小跑,马灯摇晃不定。母亲说,那是打更匠闯到鬼了。被惊醒的我,赶忙拉被子蒙了头。母亲便拍着我说,不怕,不怕。 更夫的长衫驼背,还有马灯铜锣,认我难忘。
我在重庆上学,假期回乡时,边城已经有了电灯。母亲在灯下给我做夜宵。为了省电省钱,母亲照的是小瓦数的灯泡。母亲半明半暗的背影,让我感动得默默落泪。 边城的夜市,热闹了许多,但街灯不多,街道不太亮。赶夜市的人在街上走动,与来者走近时,才看得清人,才呼朋唤友。
听故乡人说,现在边成的夜色,故乡的灯,今非昔比。于是,我回故乡,看故乡的灯,果然光彩照人,赏心悦目。街灯把街道照得通明,五彩霓虹灯光芒四射,美了街上的行人。彝族阿咪子,穿着长长的五彩百褶裙,三三五五,走在夜市上。百褶裙在她们脚下,涌起彩云,把她们美成了仙女。山外来客追着她们看。她们并不见怪,互相交头接耳,低声说话,高声笑。边城人叫彝族姑娘为阿咪子。边城的美食,在灯光下,散发出诱人的乡土味,让山外来的食客,赞不绝口。边河上架起了廊桥,灯光闪烁,像彩虹横跨在碧波之上。故乡的灯,进入了新时代。
故乡的灯,菜油灯,煤油灯,红纸灯笼,红桔子灯,马灯,霓虹灯,时代进步的脚印,让人温故而知新。 母亲已去世多年,怀念母亲,那盏菜油灯,永远亮在我心中。感悟故乡的灯,感悟国之复兴。家国情怀,伴我一生。
作者通联:成都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段明珠怡园。手机15108301780。
|  |闪小说作家论坛|手机版|触屏版|小黑屋|闪小说阅读网
( 闽ICP备2025097108号-2 )
|闪小说作家论坛|手机版|触屏版|小黑屋|闪小说阅读网
( 闽ICP备2025097108号-2 )